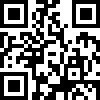2001年,郎朗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机会,原本是李云迪的,当时18岁的李云迪刚获得钢琴界的“诺贝尔”,肖邦国际钢琴比赛金奖,成为开赛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冠军。

他打破了首奖连续空缺两届达15年的成绩,也是获得这份荣誉的第一位中国钢琴家,此后,他成为了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史上最年轻的冠军和评委,足以见得音乐界对他的极大认可。
当天的《新闻联播》播报了这件事,日本NHK电视台还为李云迪拍摄了纪录片《新浪漫主义》,由于外表出众,还吸引了许多日本观众,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之下,电视台一周之内把这部纪录片播了两遍。

可当时郎朗只是借着费城交响乐团的机会回国担任独奏,中方的演出经纪人不同意,他们说,最近有其他年轻的音乐家在国际重大比赛上获了奖,郎朗在中国不是大牌明星。对于中方主办人来说,郎朗当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事后,因为费城乐团的坚持,郎朗才拿到了演奏机会。
2003年,郎朗和李云迪签下了同一家唱片公司,全世界最大的古典音乐公司DG唱片,朗朗依然是拼命的状态,每年参加120场音乐会和独奏会。而李云迪却踏入了德国汉诺威戏剧音乐学院的大门,过起了一半学生,一半演奏家的生活。

在这一点上,李云迪的母亲更是佛系代表,他说自己没什么要求,最担心的就是李云迪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活得太累。
朗朗的父亲是一位军人,也是极限鸡娃的典型代表,年轻时就有钢琴家的梦想,可惜没机会实现。当发现了儿子的天赋,他欣喜若狂,他丝毫不相信什么劳逸结合的教育理论,教育孩子向来十分铁腕。
为了逼迫郎朗刻苦学琴,甚至不惜威胁:“你不好好练琴,那你就去死”。这种暴君一般的残酷吓坏了郎朗,他对父亲充满了恐惧,他曾经整整三个月没有碰钢琴,直到父亲软言求和,他才继续开始练琴。

在郎朗的自传中,这位艺术家表达了从小力争第一名的历程,然而他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第一名只在体育竞技场里才有意义,正是他逼迫郎朗无休止地练习钢琴。
或者可以说,如果郎朗失败了,父亲郎国任会被钉入耻辱柱,或者人会嘲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自己不行就折腾儿子,失败的父母,失败的人生。
但问题是,人家还真的成功了,所以,如果以成败论英雄的话,他就成了严父出牛子,不懈拼搏阶层跨越的典型,把平民子弟逼成万众瞩目的精英。

在郎朗的讲述里,生活和艺术被描绘成由憎恨和自我驱动的权力斗争,这就是郎朗和李云迪最大的区别,他没有对方骨子里的松弛感,李云迪从学钢琴的那一刻起就写满了忧郁王子的气度,钢琴对他来说是沉浸在古典音乐里的放松,拿冠军绝非最大动力,二者分别属于两个生态圈。
如果要问李云迪和郎朗谁才是真正的钢琴大师?又该有人来撕了,所以古典音乐市场已经萎缩到只容得下一个朗朗或者一个李云迪的地步了吗?
精湛的艺术能否和当前备受追捧的浮华,空洞的表演共存,这才是我们真正该思考的问题。

对于郎朗和李云迪的battle,在艺术领域实则是没有意义的,音乐是强调欣赏性,弱竞技性的。艺术的最终本质是让我们去感受美,欣赏美。简单来说,大部分音乐是给你听的,不是给你拿来比的。
如果硬是要比,那两个同样出生于1982年的青年人,凭着天赋和勤奋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钢琴演奏家,但从曝光度来说,郎朗却比李云迪更火更红。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在电视广告的屏幕里,在网上的娱乐新闻里,总是能时不时见到郎朗。

反观李云迪就显得比较沉默了,除了一些正式的演出,很少看到有关他的报道,甚至连长相都有些记忆模糊。如今《披荆斩棘的哥哥》开播,很多人才想起来有着号大咖。对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分不清楚哪个奖项更重要,也听不出谁的演奏更具专业性。
但包装带来的红利完全超乎想象,市场很现实,朗朗早就成了劳力士、迪奥的形象代言人,这也成为一个循环,它意味着权威。一个是行云流水的音乐诗人,一个是热辣张扬的技巧天才,极具感染力。

你说孰强孰弱呢?艺术不需要第一名,把音乐还给耳朵才是我们要上的第一课。